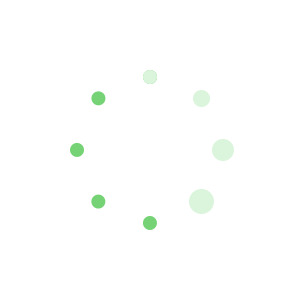本文主要论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叙述学从“经典”向“后经典”的发展变化,探讨了叙事理论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试图在文化研究的背景下提出“审美文化叙述学”的构想。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国内外逐渐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并引起了人们持续不断的关注,吸引了来自各方面人们的兴趣。这一研究从一开始就超越了纯粹“文学”的范围,渗入了传统的以及20世纪以来所出现的各种文化形式之中。它影响所及,不仅对传统的文艺学体系形成了挑战,而且也对20世纪以来所出现的一些“新”的文学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传统的文艺学体系必将发生进一步的变革,以适应飞速发展的时代。
本文主要是在文化研究这一背景下,或者说在广义的文化语境下,对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所形成的叙事理论的发展变化作一个探讨。为了适应文化研究这一趋势,同时也为了进一步丰富和扩展叙事理论,本文将提出“审美文化叙述学”的构想,以期引起人们的讨论,并就教于各位同仁。
一、从经典叙述学到后经典叙述学
现代叙事理论的形成可以说是20世纪结构主义文论的直接成果。现代叙述学的发展几乎是与结构主义、尤其是与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同步的。叙事理论早期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同时也是法国结构主义文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如罗兰·巴特、格雷马斯等,因而,现代叙事理论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打上结构主义的烙印就不足为怪了。
就叙述学研究本身而言,它主要集中于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是叙事结构的层面,它研究叙述(不论是以何种表现媒介出现的)的性质、形式、功能,并试图归纳出叙述的能力。它在故事、叙述以及二者相互关系的层次上考察叙事作品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并且探讨使它们得以相互区分开来的因素。另一个则是叙述话语的层面,它研究叙事文中话语表现模式中的时序状况与事件,集中于故事与叙述本文、叙述过程与叙述本文、故事与叙述过程之间可能的关系,而不关注故事层次本身,也不试图去建构诸如故事或情节语法。具体说来,它考察时态、语式、语态这样一些问题 ① 。
在叙述学研究中对于叙述结构的关注,是与结构主义关系更为密切的层面,用普林斯的话来说,它是由结构主义所激发(structuralist-inspired) ② 的研究层面。这一研究无疑受到了由普罗普所开启的对于俄罗斯童话故事所作的结构研究的影响。它所关注的是被叙述的故事的逻辑、句法、结构,也就是广义上的叙述语法问题。它试图要在不论以何种媒介所构成的、任何具有所谓叙述性的叙事作品中,去探寻它们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共同的叙述结构。在其早期所进行的这种努力,一如巴特在他的《S/Z》开头所说到的:
据说,某些佛教徒依恃苦修,最终乃在芥子内见须弥。这恰是初期叙事分析家的意图所在:在单一的结构中,见出世间的全部故事(曾有的量,一如恒河沙数):他们盘算着,我们应从每个故事中,抽离出它特有的模型,然后经由众模型,导引出一个包纳万有的大叙事结构(为了检核),再反转来,把这大结构施用于随便哪个叙事。 ③
巴特在这里不指名地提到了诸如普罗普以及列维-斯特劳斯等人所作研究的某些意图,它显然是沿袭结构主义研究方向的结果。这种研究状况多少反映出入们对曾经主导文学研究中那些无视对文学作品内部研究的关注所作出的反应,一如热奈特所说:“人们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文学视作一个没有代码的信息,因此现在有必要暂时将它看成一个没有信息的代码。” ④ 这些研究是以较为简单的叙事作品作为对象的,它所得出的结论在一定意义上是与他们所做的研究相符的。叙述语法的探寻对于从总体上把握叙事作品的构架与叙述逻辑自然有其不可忽略的意义,它不仅可以帮助人们对叙事作品在结构意义上的进一步理解,而且也打开了一条进入叙事作品内部研究的途径。
然而,当一定的叙述构架已经被揭示出来,一定的模式已经被建构起来之后,人们就不再满足于对这种叙述语法的一般了解,而将其研究深入到叙述本文中,探讨叙述本文中的话语表现模式以及故事与叙述话语之间的关系等。热奈特所进行的研究,尤其是他的《叙事话语》的发表,不仅是这一研究的一个重要起点,同时也为这一研究方向的确立打下了一个重要基础。它日益形成为叙述学研究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主流,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得到了充分发展,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形成为人们现在称之为“经典”叙述学的阶段。除热奈特而外,里蒙-凯南,巴尔、查特曼、普林斯与斯坦泽尔等人的研究大体上都属于这一范围。这些研究继承了早期叙述学研究中已有的成果,但又与早期的研究明显不同。他们不再试图去探讨无边无际的具有所谓叙述性的一切叙事作品、包括用各种不同媒介表现出来的叙事作品的基本叙述语法,而主要基于以语言形式出现的叙述本文为其研究对象,而且更多地是以大量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小说作为研究对象,来探讨在这样一些叙事作品中所显示出来的叙述性以及叙事话语中的种种形态。由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叙事作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其所取得的成绩和具有的影响上都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因而,基于对这样一些叙事作品所作的叙述学研究无疑为叙事理论的实践与运用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而理论研究本身也一直在不断拓展与深化之中。
与叙述语法的研究一样,基于叙事话语的叙述学研究仍然将其研究的范围限定于叙述本文之内,专注于一种按照二元对立原则所界定的形式概念或范畴的研究,而并不考虑它与超越叙述本文这一范围的外在关联。在叙事理论研究的过程中,人们逐渐意识到这种纯粹形式意义上的研究所具有的局限性,早期叙述学研究中的一些偏激的、绝对化的理论倾向受到了或多或少的质疑。比如说,托多罗夫诗学观点的变化就是一例。在托多罗夫于1973年再版的《诗学》一书中,他对1968年原版中的最后一章作了重大修改。该章原名为“以自身为对象的诗学”,强调诗学的对象限于其自身这样一种方法。而在1973年的再版中,这一章被改名为“作为过渡的诗学”,认为文学是一个开放的实体,对文学的研究应当过渡到对一切本文和象征系统的研究。同时,决定文学特性的因素恰恰不在于文学自身之内,而在其自身之外。因此,在话语科学业已创立的情况下,诗学应当注意寻求促使人们将某一时代某些作品列为文学作品的原因 ⑤ 。对于那种将本文孤立于产生本文的外在因素而进行研究的意图与方法,一些有识之士则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批评。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荷兰乌德勒支大学教授佛克马在谈到新批评与分解主义时说到,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分解主义的解释同新批评的解释有某种相同之处,二者的差别主要在于,新批评断定文本有其统一性和相干性,而分解主义则假定,互文关系线索可能比文本本身的词语更为重要。他说:
分解主义者认为,世界是由文本组成的,因而他们沉溺于文字游戏的象牙塔里。他们知不知道,这世界除了文本之外,还有人,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们在受苦挨饿!他们却抛弃了历史感和社会责任感。这实际上是一种语言帝国主义主张!
佛克马明确指出,“文学必须和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文学再也不是一个隐蔽的、‘自律的’领地了,文学研究的对象也不能仅局限于文学文本。” ⑥ 在叙事理论不断拓展的过程中,人们日益意识到它所具有的某些理论导向已经成为它继续发展的桎梏。不冲破人为地设定的一些疆界,就无法使它得以进一步发展。1989年,里蒙·凯南在谈到“叙述学”的时候曾经说到,在她(以及大多数运用这一术语的人)看来,叙述学是60年代与70年代早期,在结构主义及其形式主义的先驱的支持下主要在法国发展起来的叙事理论,然后,这一理论于70和80年代早期在英语世界被介绍、运用、改善与加以综合。“接着呢?”她问道,然后她回答说:按她的看法(尽管不是每个人都同意),“它开始逐渐低落。”而她认为低落、甚至于出现危机的原因可能就在于人们已经倦于做一件事情而希望做点儿别的什么。她所指的也就是基于传统分析模式的叙述学研究忽视了一系列与叙事话语相关联的问题,包括与超越语言媒介之外的符号系统如绘画、电影,甚至于意识形态等这样一些相互关联的问题 ⑦ 。对于所存在的这一系列问题,罗斯·钱伯斯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叙事作品的语境——没有认识到叙事是一种社会存在,一种影响人际关系并且由此获取意义的行为:叙事之所以成为叙事,依赖于一种隐含的社会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使得叙事作品与社会之间具有一种交换性质,而交换就意味着存在于社会的欲望、目的和各种制约力量之间的综合关系。” ⑧ 他强调叙事作品与外在于它的社会、人际关系等的不可分性,实际上是要破除叙述学画地为牢将自己的研究仅仅限制在本文之内的这种局限,将它的批评视野加以扩充。
在这样一种理论趋向下,文学研究出现了某些转变,从强调对作品内在的本文研究转变为不仅仅关注对本文内在的研究,同时也关注对本文与其外在关联的研究。反映在叙事理论的研究中,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文化研究这一背景下所出现的叙述学研究、即所谓后经典叙述学研究(post-classical narratologies)中,这种理论转变产生了明显的反应。叙述学跳出了长期以来将其自身限定于叙述本文内在的封闭式研究的窠臼,在保持其自身的理论特征和特有的理论模式的同时,它与诸多外在要素相关联,并与已经存在的大量其他的研究方法,诸如女权主义,巴赫金主义,解构主义,读者反映批评,精神分析,历史主义,修辞学,电影理论,话语分析以及(精神)语言等相沟通,从而形成叙事理论研究融会贯通、向纵深发展的局面,由此相应出现了叙述学研究中的各种变形。大卫·赫 尔曼1999年主编出版了《叙述学:叙事分析的新视野》 (Narratologies: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一书,书名中的“叙述学”一词使用了复数就是对这种局面的最好反映。在赫尔曼看来,叙事理论所经历的不是它的终结而是持续的、有时令人吃惊的变形,“在互相渗透的年代里,叙述学(narratology)实际上已经分枝为叙述学(narratolo-gies);结构主义关于故事的理论构建发展成为叙事分析中的多重模式” ⑨ 。他认为这些模式与结构主义传统或多或少保持着一种批评与反省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单一的叙述学出现了诸如电影叙述学(filmnarratology),音乐叙述学(musical narra-tology),女性主义叙述学(feminist narratology),社会叙述学(socionarratology),以及在一个因特网盛行的时代的电子叙述学或电子网络叙述学(cyberag narratology)等等。这些叙述学的分支在各自关注的领域里开展着自己的研究,它不仅丰富了叙述学,也为叙事理论更好地适应和反映这一迅速变化的时代而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这些研究中,人们力图对叙述学研究的经典模式重新思考与构建。从而,叙述学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和拓展。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已经倾向于摈弃传统叙述学研究中将叙述本文视为一个封闭体系的模式,而按照认识论的标准重新界定叙述性,并超越形式叙述学而进入语用学、接受理论的领域,强调读者和语境的重要作用,以及读者的接受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试图构建出一种有机的阅读状况。
与传统叙述学相反,这些研究力图使自己的探讨具有文化的、历史的观念和历史的意义,而不只具有形式的意义。莫妮卡·弗鲁德尼克的《走向“自然”叙述学》一书中明确宣称,要按照认识(“自然”)的标准重新界定叙述性,而且,“不像大部分其他的叙事理论,这一新的模式是明确而有意地属于历史的。”这种历史性从标题中的“走向”一词中就已经反映出来。它不仅反映了已经提出的这一认识与有机的模式开始具有的性质;它也涉及到了各章构成的时间先后顺序的轨迹,从口头语言的故事讲述到中世纪的,早期现代的,现实主义的,现代主义的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写作类型 ⑩ 。按照文化地、历史地出现的不同的叙事作品来进行研究,在这一广阔的文化、历史背景下来探讨不同的叙事作品所具有的特征,这本身就具有一种浓重的文化与历史感。
在这一研究的扩展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人们不仅在进行着叙事理论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以扩大其研究的视野;同时,也将叙述学研究中叙述本文的范围加以延伸,扩展到那些传统的经典叙述学很少涉及的领域。这种努力,在莫妮卡·弗鲁德尼克的《走向“自然”叙述学》一书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作者声称,在该书中“与‘经典’叙述学相反,不是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小说占优势的观点来探讨叙述性,而是从那些迄今为止较少吸引人们进行分析的话语类型来探讨叙述性”,这就是口头与拟口头故事讲述类型,包括会话叙述和口头讲述史,历史写作,书面叙述的早期形式(中世纪诗体史诗,中世纪历史与圣徒行迹,14到16世纪早期书信中的故事讲述,伊丽莎白时代到贝恩11 时的叙事文);以及属于另一端的范围,即后现代主义文学。后一领域包括一些广为人知的写作模式,诸如中性叙述与现在时态小说,此外,还包括第二人称小说与用“我们”形式叙述的小说,或以“它”,“一个人”,“人”叙述的本文;以及自贝克特到莫里斯·罗切(Maurice Roche),和由克拉丽斯·利斯佩克托尔(Clarice Lispector)12 ,克里斯塔·伍尔夫所创作的实验写作。作者指出,强调这些被称之为非正规形式(non-canonical forms)的叙述(非正规,指的是在现今小说理论研究的范围里),“旨在引起对现行的一系列叙述范式的某些修正,同时也对关于经典模式的基本设想提出某些重要的方法论问题。这样,非正规叙述的分析就为故事讲述模式的新的重构开辟了道路,从而提出一种基于认识标准和读者反应框架的新的叙述学范式,它对于虚构与非虚构的叙事类型都是适应的。从这一视野出发,经典叙述学的现实主义基础就可以超越将现实主义作为特定模式范例,也就是让模仿阐释的阅读策略得到充分运用的分析方向。”13
从上面的这些叙述学理论发展趋向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传统叙述学理论的超越,也可看出某种批评的循环,比如,在叙述学的早期研究阶段,人们曾试图从大量具有所谓叙述性的不同媒介的叙事作品中来概括出叙述语法与叙事话语的某些规律,但是,这种尝试因为过于雄心勃勃而又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撑而并未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尽管后来像查 特曼在其《故事与话语:小说与电影中的叙事结构》(Story and Discourse:Narrative Structurein Fiction and Film)对电影这种特殊的叙事作品进行过一些有意义的探讨,这种研究毕竟十分有限。而在叙述学的发展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理论资源、已经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理论分析模式的时候,这种扩大其研究范围的意图,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成为这一新的理论潮流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二、叙事理论与文化和文化研究
在传统的叙述学研究、尤其是早期的研究中,由于其研究对象被严格地限定在叙述本文之内,因而与之相伴的是它竭力排除与社会、历史、文化等相关联的要素,排除读者在某一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对作品的接受,排除与作者的创作意图、思想观念密切相关的各种因素。上述这些因素都与传统的“文学”这一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因而在叙述学研究中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人们几乎看不到叙事文学一词,转而出现的只是叙述本文、本文,以及叙事作品这样的概念。
我们知道,叙事作品与其他任何文学作品一样,本身就属于一种思想交际活动,即一种社会文化的活动。一部作品不可能离开创作主体,离开与其他作品的参照而存在,也不可能脱离特定的社会文化范围而独立特行。就叙事作品的结构形态而言,应该意识到,结构形态总是难于说明和论证其自身,它总要诉诸于其他非形式的东西。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探讨“作品如何说”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但如果在探讨了这样的问题之后,再继续探讨“作品为什么这么说”应该会显得更为完备、更有意义,也更有说服力。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既能对结构形态这一类问题进行精细的研究,同时又关注结构形态背后的文化符码,关注更大范围内的文化审美问题,我们将会更深入地理解文学作品。
在文化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的情况下,对于叙事作品文化层面的关注,或者说注重在文化层面上开展对叙事作品的研究,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一点,在米克·巴尔1997年出版的《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修订第二版中有明显的反映。第二版与1985年出版的英文第一版相比,不仅在篇幅上增加了约三分之一,而且作者进行了大量修改,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作者扩展了她理论模式的范围,更新了有关文学叙事的章节,并从文学研究的领域以外增加了许多新的例证。这些特别增加的部分包括对于下述问题的讨论:叙述中的对话,作为转换的传译(包括不同媒介之间的转化),互文性,多媒介的渗透,以及叙述学中主体的地位等。在关于视觉形象和以艺术和电影为例的视觉叙述,以及从人类学视野进行考察的叙述这两个全新的章节中,作者根据叙述学在文学领域之外的应用,对它们进行了重新评价。作者拓宽了传统叙述学的视野,一改传统叙述学致力于形式分析的趋向,而将其探讨的范围深入到文化分析这样一个更加宽泛而又实际的领域。在原有的三章之外,作者增加了第四章:“叙述学的文化分析运用”。她所追寻的不只是传统叙述学中“话语来自何方,以及谁将它们说出来”,而是广泛的文化范围内的问题,它包括“恨,爱,赞美,反对的论辩,震撼,或敬畏”等,这不仅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新的开拓,也是叙事理论在文化研究这一理论潮流中的具体反映。
巴尔所作的这种努力,在她对“叙述学”这一学科概念所作的界定中可以看得出来。在原来的版本中她所作的界说是:“叙述学是关于叙述本文的理论。”14 在新版中的界定是这样的:“叙述学是关于叙述,叙述本文,形象,事像,事件,以及‘讲述故事’的文化产品(cultural artifacts)的理论。”15 这里不仅将原先的一个简单界定加以扩展,而且特别强调了对于“文化产品”的研究,这样一来,其适用的范围就远为扩大了。原版中对本文的界定是:“本文(text)指的是由语言符号组成的一个有限的、有结构的整体”16 ,而在新版中,巴尔紧接着上面的文字增加了这样一段话:“符号的这一有限整体并不意味着本文自身是有限的,因为其意义、效果、功能与背景并不是有限的。它仅仅表明这里有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词,或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电影中的形象,或绘画中的构架被加以确认。即便存在着这样一些界限,如我们将看到的,它们也不是极为严密、滴水不漏的。”17 通过强调“其意义、效果、功能与背景并不是有限的”,实际上已经使本文超越了单纯意义上的本文范围,而对于诸如“电影中的形象,或绘画中的构架”这样一些“本文”加以确认,也就扩大了原先单纯的“叙述本 文”的范围。
巴尔认为,解释既是主观性的也是易受文化发展影响的观点不仅将叙事分析转化为“文化分析”的活动,也使解释的过程更具普遍兴趣。这种情况即使在人们的研究对象仅仅是文学的时也会出现。为了强调这一点,她在本书中所有以语言出现的文学例证中还杂以采用其他媒介的一些例证,比如,在“本文”这一章里,她以一位当代艺术家肯·阿普特卡尔(Ken Aptekar)的一幅称为《我六岁》的画作为分析对象18 ,同时也在详细研究的情况下不时对文化现象的重要性作出评论。
巴尔之所以增加“叙述学的文化分析运用”这一章,是因为她越来越意识到叙述所包含的文化内涵的探讨的重要性,并且试图阐释叙述学与“文化研究”(她更倾向于称为“文化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她看来,当下对叙述学的新的回归是一个极受欢迎的现象。但这一回归何以会发生,何以是现在,这一点并不十分清楚。她作了这样的推测:“一个首要的理由可以简单地归之为叙事的文化分析的普遍出现,它在逻辑上自然要呼唤一种对其进行处理的方式。”就像符号学一样,叙述学有效地适用于每一种文化对象。并非一切“是”叙事,而是在实践上,文化中的一切相对于它具有叙事的层面,或者至少可以作为叙事被感知与阐释。除了文学中叙事种类的明显优势而外,随便就可以想到叙事可能会“出现”的许多地方,它包括诸如诉讼,视觉形象,哲学探讨,电视,辩论,教学,历史写作等。叙事的多种存在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只有在我们整个地或部分地限定为叙述的文化产品中叙事是决定性的时,叙述学的重要性才得以存在。
在巴尔看来,叙述学并不只是要证明对象的叙事性质。同时,叙述学也并不是一种工具,至少,不是对于知识的“现成”产品。叙事是一种文化理解方式,因此,叙述学是对于文化的透视。在文化研究的时代,叙述学应该在理解文化研究这一行动中显示出本文与阅读、主体与对象、作品与分析之间的相互关系。换句话说,它能够在任何文化表达中,在没有任何特惠的媒介、模式或运用的情况下,区分出不同的叙事所在地,区分出其相对的重要性,以及叙事对于读者、听众与观众的不同效果。一种详细说明与描述叙述性的理论并不是叙事,不是类型或对象,而是一种文化表达模式。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文化产品、事件,或其活动的范围可以详尽地加以分析19 。
作为文学讲究的叙述学,从大的范围来说,是一种文化活动,它本身与人类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叙述学已经得到充分发展,叙述语法、叙述结构、话语分析的众多模式等等已经得到充分展现的情况下,叙述学就没有必要再继续画地为牢,使自己继续在原地打转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叙述学与不同学科之间所产生的交叉研究,叙述学对文化领域这一更为宽广的范围的渗入,无疑会使它获得新的无限生机,并在这一新的发展过程中在理论上得到进一步完善。
三、构建审美文化叙述学
在已经存在的叙述学发展的众多分支,诸如电影叙述学、音乐叙述学、女性主义叙述学、社会叙述学、电子网络叙述学等这样的情况下,我希望在一个新的方向和范围中,在文化研究这一背景下,提出一个叙述学分支的构想,这就是审美文化叙述学(culture-aestheticalnarratogy)。从大的范围来说,审美文化叙述学仍然属于叙述学这一总体框架之内,更确切地说,它属于赫尔曼所说的在适应大量的方法之后,叙事理论所经历的“变形”20 。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对叙事理论的一种重建,不是对叙事理论作某种根本性的调整,而是在它已有的发展基础上,作一种适应性的变化,即开始叙述学的一个新的“变形”。
审美文化叙述学将坚持叙事理论总的发展方向,运用现行叙事理论中已有的基本理论模式和方法,对叙事作品,或者说叙述本文进行分析。这一基本方向无可改变,否则,叙述学研究的一系列特征和机制将会丧失。但是,与上述各种叙述学的分支一样,审美文化叙述学同样存在着力图扩大它的研究范围并确立自身独特的研究方式的意图。
就研究范围而言,审美文化叙述学将超越传统纯粹意义上的叙事作品或叙述本文,而将其范围延伸至文化意义上的叙事作品,无论这种叙事作品是以什么样的媒介形式出现的。在这一点上,我赞同巴尔在将叙述学运用于文化研究时对研究对象、即她所界定的“叙述本文”所下的这一不同于先前的 新的定义:“叙述本文是叙述代言人用一种特定的媒介,诸如语言、形象、声音、建筑艺术,或其混合的媒介叙述(‘讲’)故事的本文。”21 这就意味着,众多具有叙述性的文化产品均可进入研究的视野之内。除了以语言为媒介的叙事作品,如小说、戏剧、叙事诗、神话、史诗、童话、民间故事等,还可以包括诸如音乐、绘画、建筑、电影、电视剧、民歌、舞蹈等文化产品,只要在这些作品中包含有“讲述故事”的意义。当然,从实践的意义上看,以语言媒介为载体的文化产品免不了仍会在研究对象中占据重要地位。
就确立这一研究独特的研究方式而言,应该说,对特定的研究对象,即广义的叙述本文进行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审美研究,这是我所提出的审美文化叙述学的关键之点。也可以说,这是要从审美意义上来对众多的文化产品进行叙述学研究。从这个切入点出发,可以将审美文化叙述学简单地称之为审美叙述学(aesthetical narratology),以强调其审美的价值意义。
我们知道,在传统的叙述学研究中,研究者被要求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去对待其研究对象,对诸如叙事作品的结构形态、叙述语法等作客观的描述。这种描述注定要忽略决定每部作品艺术价值的具体成分,注定要避免对作品作出审美的价值判断。传统叙述学力图避免涉及作品的价值意义等文学的形而上层面,并意图以此避开对一些涉及价值意义的问题的纠缠,自然与其学科理论特征相关。但这样一来,它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文学作品、包括叙事作品中,涉及价值的、审美的、心理的这样一些文化意义上的因素无所不在,去掉这些因素,文学的魅力就将丧失,文学作品就不成其为文学作品。而完全抛弃审美价值判断的文学研究不仅将使研究的价值减色,使研究的路子越走越窄,也会令研究的成果逐渐趋于枯竭。实际上,这也正是传统叙述学研究在取得一系列成果之后,难以在原有的轨道上继续向前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审美文化叙述学或者说审美叙述学正是要避免这种片面的、机械的观点。它在对对象进行叙述学研究时,不仅不回避对叙述本文的审美价值判断,而且还有意探索叙述本文中所存在的这种审美价值意义,以及透过形式意义之外的诸如心理的、意识的、思想的、社会的意义,也就是广义上的文化意义。这样一来,就可以在坚持叙述学研究透视的情况下,使这种研究变得更为深入、透彻,不仅具有形式上的价值意义,同时也具有更大范围内审美文化上的意义。这样的研究可以在叙述学的构架下,从相互关联的不同层面去对对象加以把握,同时,将这些相互关联的层面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它可以从下述这样一些层面去对对象进行审美文化意义上的分析和研究。
形式层面。形式美是审美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而有机的组成部分。叙述学以对叙述本文形式意义上的研究而著称,它深入叙述本文内在的组织结构,探究其内在的形式上的构成、组合,各个部分如何发生作用,各个部分组合在一起如何产生效用,也就是说,在叙述本文中叙述故事的时候,探讨它是“如何说”的问题。这样一种探讨,本身就具有形式审美的意义。只不过在传统叙述学研究中,这种探讨被视为研究的目的与终点,而在审美文化叙述学中,它被看作为一个重要的层面,但却不是惟一的层面。一般说来,我们在探讨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现象时,只有落实到相对稳定的文学形式层面,才能够描述一个时期的文学发展规律及其特有的审美内涵。在探讨特定的叙事作品时,形式层面本身同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形式从来不只是一种表层的文学征象,而是在更深层次上标志着社会历史的本质内蕴。透过叙述本文形式审美的层面,人们完全可以从中发掘出审美意义上更多深层次的内涵。人们可以在形式层面的基础上,将相关的研究继续进行下去。
社会历史层面。任何叙述本文,都不可避免地存活在人类所生活的时间与空间中,它既是由人所创作也是为了人而创作、为了人而存在的,而人是历史地存在的。因而,成功的艺术作品不仅具有永恒的审美艺术价值,也是与特定的社会历史不可分离的,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氛围下的产物。人们无须人为地割断叙述本文与产生它的社会历史关系、与历史的人之间的关联,而可以将对叙述本文内在的形式审美进一步加以扩展,在探讨它“如何说”的时候,再探讨它“何以这样说”这一类的问题。比如,在谈到中国传统小说时,我们知道,所谓零聚焦叙事在长时间里几乎一统天下。叙事作品中的叙述者几乎都以第三人称出现,通过所谓无所不知的叙述者来进行叙述。即使是自传性的叙事 文,大多数也将第一人称让位于第三人称。在司马迁《史记》结尾部分的自传中,司马迁用第三人称自称为“迁”;而在用到第一人称“余”时,也往往以“太史公曰”作为先导。在蒲松龄的大量短篇小说中,叙述者往往在结尾以作者的身份和口吻发表意见,以作针砭论赞,这里的叙述者同样避开了第一人称的形式,自称为“异史氏”,冠之以“异史氏曰”作为引导。这种情况的出现应该说与中国传统的“中庸”道德观念是分不开的,与老子“道可道,非常道”那种真相只能暗示而不能直接表达的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将这种哲学与道德观念运用到社会生活领域,就意味着各方面要适中;将这种思想运用到美学领域,就意昧着重要的不在于艺术家能表现得多么细致详尽,而是通过细节能暗示出多少启示22 。因而,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含蓄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审美概念。公开地、直接地、详尽地谈论自己,并不符合传统的中国思维方式与美学方式,也不符合传统的道德观念,这可以看作为中国传统叙事作品中第一人称的使用十分欠缺,而第三人称叙述者广为流行的原因之一。
精神心理层面。在这一层面上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探讨。一个方面关系到作者创作的精神心理因素,另一个方面则涉及到读者对叙事作品接受的精神心理因素,它主要与审美体验相关联。在叙述学研究中,长期以来都力图切断作品与其创作者的关联。表现在叙事作品中,这样一种观点长久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就是客观的、非人格化的显示这种叙事方式要高于任何允许作者或他的可信的叙述者直接出现的方法。但实际上无论作者选择以什么方式来讲述故事,他或她与作品的关联都难以割断,“虽然作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他的伪装,但是他永远不能选择消失不见”。“不论一位非人格化的小说家是隐藏在叙述者后面,还是观察者后面,是像《尤利西斯》或者《我弥留之际》那样的多重角度,还是像《青春期》或康普顿-伯内特的《父母与孩子》那样的客观表面性,作者的声音从未真正沉默。”23 尽管我们不能将叙事作品的叙述者与作者任意关联,甚至将叙述者与作者等同起来,但是作品与其创作者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在创作叙事作品时,创作者采用什么样的形式,采取什么样的叙述者,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叙述故事,不仅与特定的时代,也与创作者的精神心理因素相关。至于读者在阅读或欣赏叙述本文时所经历的审美体验,同样受制于叙事作品的特定形式,比如说,叙事作品中所出现的是一个可信的叙述者还是一个不可信的叙述者,是一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还是一个参与故事的人物叙述者,对于读者或观众来说会产生不同的精神心理感受和不同的审美体验。
文化积淀层面。任何一种文学艺术形式都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长时期文化积淀之下的产物,表现在叙事作品中也不例外。这种文化积淀造成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国家和地区会产生某些特定的文学艺术形式,或者某种形式盛行而其他的形式却受到抑制。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可以看到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下所出现的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与无限丰富的叙述本文。
除此而外,审美文化叙述学还可以从其他相关的不同层面对叙述本文进行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使这一新的叙述学“变形”更为完备、更富于科学性。任何一种理论既有其特定的发展方向,同时这一理论本身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某种意义上,上述审美文化叙述学研究所渗透的层面,除了形式层面而外,都在消解传统的经典叙述学所赖以存在的二元对立法则这一基础,以及一些人为地设置的限定。只有消除这些构成传统叙述学理论中必不可少的基础和限定,才有可能使叙述学理论和研究在理论的潮流中得以有效而又富于成果地继续发展下去,而叙述学理论和实践事实上已经在它的各种“变形”中被证明是充满生机、富于活力的。在文化研究这一理论潮流的背景下,审美文化叙述学也应该在叙事理论的发展与实践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并逐渐显示出它自身特有的力量。
注释
①②见Gerald Prince,A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7,p.65.③[法]罗兰·巴特,(S/Z),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④[法]热奈特《结构主义与文学批评》,载《辞格一》,巴黎瑟依出版社,1966年版第150页;转引自张寅德《法国结构主义文论的嬗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⑤见张寅德《法国结构主义文论的嬗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⑥见王宁《关于文学史、文学理论及文学研究诸问题——访著名学者佛克马教授》,载王宁《比较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186页。
⑦Shlomith Rimmon-Kenan,“How the Model Neglects the Medium:Linguistics,Language,and the Crisis of Narratology.”The Journal of Narrative Technique,19/1(Winter1989),pp.157-166.
⑧Ross Chambers,Story and Situatio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p.4.转引自王丽亚《分歧与对话——后结构主义批评下的叙事学研究》,《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第32页。
⑨David Herman,“Introduction:Narratologies.“Nar-ratologies: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ed,by David Herman,Columbus:Ohio University Press,,1999,p.1.
⑩Fludernik Monika.Towards a“Natural”Narratology. London:Routledgc,1996,p.xi.
11贝恩(Aphra Behn1640-1689),英国戏剧家、小说家、诗人。
12克拉丽斯·利斯佩克托尔(Clarice Lispector1925-1977),巴西女小说家。
13Fludernik Monika.Towards a“Natural”Narratology.London:Routledge,pp.xi-xii,1996.
14 16[荷兰]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谭君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15 17 18 19 21Mieke Bal.Narratology: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Second Edition.Toront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9,p.3,p.5.pp66-75.pp.220-222.
20见David Herman,“Introduction:Narratologies”.Narratologies: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ed.,by David Herma,p.1.
22见[美]王靖宇《〈左传〉与传统小说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6页。
23[美]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3页。
来源:网络整理 免责声明:本文仅限学习分享,如产生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在文化研究的背景下提出“审美文化叙述学”》
由互联网用户整理提供,转载分享请保留原作者信息,谢谢!
http://m.bsmz.net/gongwen/155865.html
- 上一篇:失败的滋味美文
- 下一篇:最美好的相遇美文